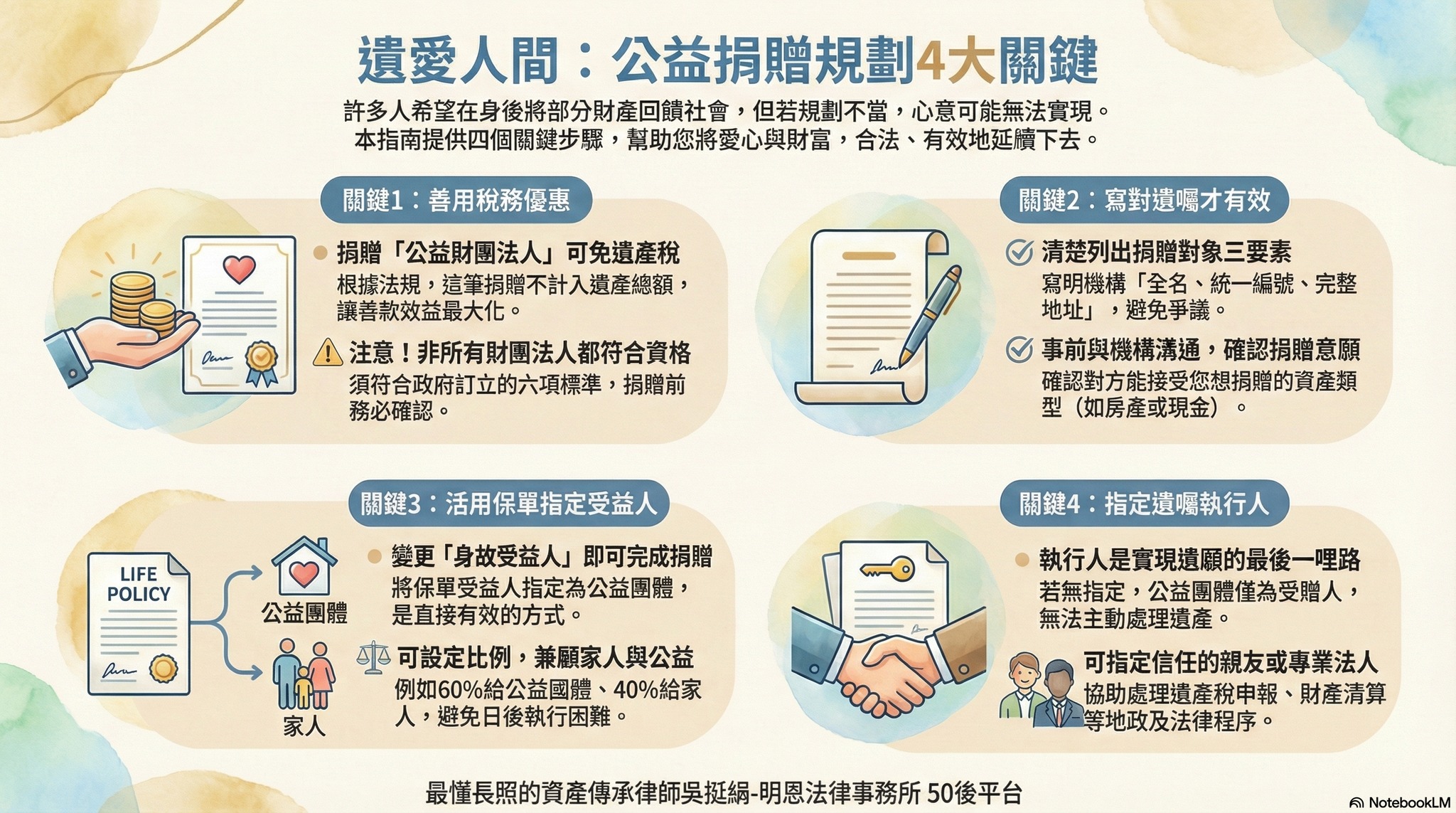醫學強化了生存能力,是否也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-有權拒絕急救-《二十一世紀生死課》
醫學強化了生存能力,是否也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-有權拒絕急救-《二十一世紀生死課》
暫不討論酷刑凌虐等不人道行為,人對死亡的恐懼大致可以分為兩種:對死亡本身的恐懼,以及恐懼死亡到來之前必須承受的折磨。現在是怎麼回事?難道我們恐懼死亡又多了一個理由——恐懼心肺復甦術?
愛長照編輯團隊
2019/03/04
瀏覽數 15,140

文/海德・沃瑞棋
醫學幾千年來始終是門藝術,直到現代才成了科學。在科技與醫學結盟後,醫師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呈等比級數倍增。在此同時,各式各樣的新發現也傾巢而出,大幅扭轉人類對於生命的既有認知。X光造影和斷層掃描的發展,讓原本不切開身體便無從發現的疾病無所遁形。
一九五三年,詹姆斯・華生(James Watson)和弗朗西斯・克立克(Francis Crick)在《自然》期刊上發表驚天之作,揭示了生命基本要素DNA的祕密。面對疾病,我們現在不但使用抗生素等新藥物,也研發出制敵機先的疫苗防患未然。目前世上除了三個國家之外,小兒麻痺症疫苗已將這種疾病澈底根除。
然而,醫學固然強化了我們的生存能力,卻也開始侵犯人類死亡的權利。
一九六〇年代後期,一名六十八歲的英國醫生被診斷出胃癌。他之前因為心臟病發已經退休,但健康情況還是沒有好轉。他接受手術切除胃部,但效果不佳,因為癌細胞已全身擴散。腫瘤壓迫他的脊椎神經,奇痛無比,即使嗎啡開到最高劑量也舒緩不了。手術結束十天之後,他整個人垮了,肺部也出現大型血栓。
一位年輕醫生當機立斷,冒險開刀移除動脈血栓。老醫生恢復意識後,一面感謝醫療團隊盡心照顧,卻也懇請他們滿足他的心願:下次他再心臟病發,請別再為他急救了。
他實在痛得受不了,也幾乎沒有讓他輕鬆一點的辦法。他心意已決,也明確表達意願,甚至還親自在病歷上註記,並一一告知醫院員工:他再也不要接受心肺復甦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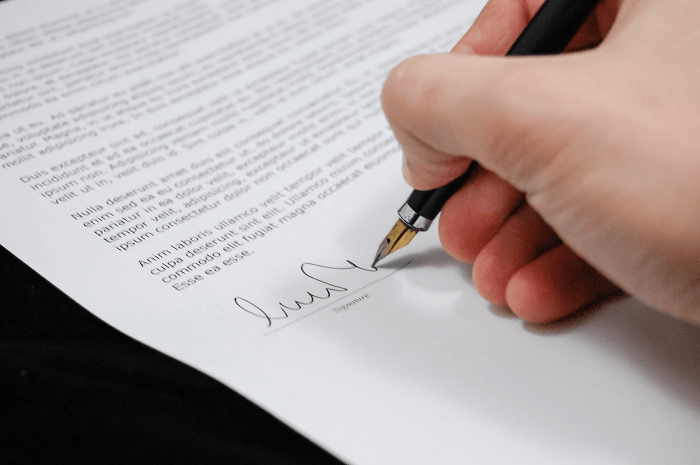
(圖片來源:pexels)
然而,即使他再三提醒,醫護人員也都知道他的意願,他兩個禮拜後再次心臟病發時,還是一晚上就被施以心肺復甦術四次,脖子上還開了造口幫他呼吸。不過這次心臟病發十分嚴重,他命是救下來了,但整體情況已幾乎不像個人。
他的大腦無法有意義地發揮功能,他也不斷癲癇發作和劇烈嘔吐。然而,醫護人員還是繼續為他治療,繼續施打抗生素,繼續全力維繫他的生命,直到他心臟停止那天。
從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,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。只要看看一九六九年一名英國醫師的投書,便能了解當時醫界的普遍氛圍:
『只要有擊退死亡的機會,吾等絕無不全力迎擊的道理,不論病人和家屬需要付出的代價多高,都不該怯於艱苦投降認輸。暫不討論酷刑凌虐等不人道行為,人對死亡的恐懼大致可以分為兩種:對死亡本身的恐懼,以及恐懼死亡到來之前必須承受的折磨。現在是怎麼回事?難道我們恐懼死亡又多了一個理由——恐懼心肺復甦術?
我輩醫者一向認為:行醫濟世的最大風險是犯下致人於死的錯誤。難不成規矩變了?現在最嚴重的過失怎麼好像是讓病人活下來?』

(圖片來源:pixabay)
醫生們既陶醉於醫學發展一日千里,卻也對前所未見的處境茫然若失。醫學的每個領域、每項專業都在突飛猛進,醫界先賢未竟的夢想似乎就要化為現實。打從懸壺濟世成為一門志業以來,代代醫者無不費盡心思想延長他們患者的壽命。可是,延年益壽的長期效應會是如何?他們從沒仔細想過。
科技發展也大幅改變醫病關係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,醫生原本習慣在家中或診所為病人看診。大戰結束後時局穩定,醫學知識與科技進展日新月異,但隨著醫院掌握的治療與檢驗方式越來越多,它們也更有能力醫治病情嚴重的患者,於是,醫療照顧的陣地從診所轉往醫院。
問題是,醫生和病患的距離不但未能拉近,醫院的運作方式還進一步破壞醫病關係。越來越多醫師太依賴檢驗報告和掃瞄影像來了解病人,對他們的病情也常依標準程序照表操課。簡言之,科技反而讓醫生和病人更加疏遠。
這股風潮恰好與一九六五年聯邦醫療保險生效同時出現,原因很可能是醫療補助讓大批病患得以就醫。醫院不得不增加每位醫生診治病患的人數,而隨著文書作業暴增,醫生能用在病人身上的時間也越來越少。

(圖片來源:pixabay)
醫學獲得科學加持之後,醫生的知識基礎也更為扎實,過去不甚了了的生理機制如今能倒背如流。不過,很多醫生也因此變得心高氣傲,像精通玄義奧理的專家一樣不可一世、目中無人。這種情況在一九六〇年代尤其嚴重,醫生和病患的心思幾乎毫無交集。
事實上,一項一九六一年進行的調查顯示:不贊成告知病患確診癌症的醫生,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。當時進行的其他調查也顯示同樣的結果。大多數醫生認為:之所以不該向病患透露病情,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讓他們保持希望。如果病患的情況已不得不接受手術或放射線治療,醫生還是會盡量避談「癌症」,改稱「腫瘤」或「癌前期病變」。
耐人尋味的是,病患的想法截然不同。在研究中受訪的病人裡,絕大多數表示他們想知道自己的確切病情。醫界就像當時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,行事風格深深充滿父權色彩。
有位醫生曾在大名鼎鼎的《刺胳針》上講過:「男醫生和女醫生的職涯展望之所以不同,有些因素是心理上的,有些因素是生理上的,而當然,社會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小覷。」這位醫生接著引用史蒂文・戈德堡(Steven Goldberg)一九七七年的著作《父權之必要》(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),指出女性由於缺乏男性荷爾蒙,所以沒有爭強好勝的動力。

(圖片來源:istock)
這種父權式的威權態度,對病人造成嚴重而惡劣的影響,對時日無多的病人傷害更大。對於應該採取多激烈的手段來治療病人,大多數醫生常片面決定,不容他人置喙,而他們的處理方向往往天差地遠,有極其激烈的侵入性治療,也有盡量簡化的緩和性處置。即使有些病人明確表達不做積極治療,有些醫師還是充耳不聞,執意進行激烈治療;但另一些時候,醫生又會自行認定病人已無藥可救,繼續治療毫無意義。
事實上,早在急救倫理引起全美熱議之前,有些醫院已經開始將治療判斷標準化。例如在紐約皇后區的一間醫院裡,如果醫師判斷某位病人身體太過虛弱,撐不過心肺復甦術,或是不太可能從心肺復甦術得益,他們就會在那位病人的病歷貼上紫色貼紙。
這其實賦予醫生很大的權力,讓他們只依主觀判斷就能決定醫療方針,就能決定一名病人值不值得施予心肺復甦術。而且,他們很少把這些決定告知病人或家屬。
另一個日益普遍的作法是所謂「怠速代號」(slow codes)。這種急救程序也叫「做做樣子」、「演一下」、「淺藍代號」或「好萊塢代號」,要是醫生判定病人太虛弱或病情太嚴重,就會用上這種方法,因為萬箭齊發的「藍色代號」對他們已經沒幫助了。
雖然這些考量有時是出於人道,不希望急救措施對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,但更多時候是醫生和病人或家屬雞同鴨講,完全沒辦法溝通,醫療人員只好「做做樣子」安撫一下家人。
由於「怠速代號」既尷尬又曖昧,醫療人員從不公開討論,頂多只在走廊上低聲交換意見。
繼續閱讀:
1. 給希望善終的你,叫救護車急救之前,必須知道的事
2. 「如果不急救,親戚和家人都會怪我不孝……」這是孝順真正的意義嗎?
更多《二十一世紀生死課》的文章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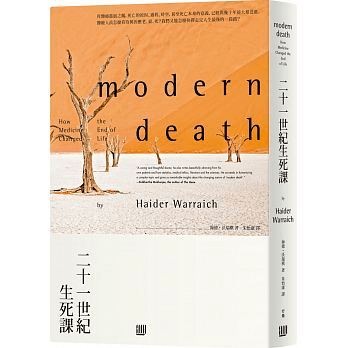
《二十一世紀生死課》
作者/海德・沃瑞棋
本文經行路出版社同意後轉載,本書更多的精彩內容,請按此了解
―
分享
文字
100%
120%
140%

.jpg)